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与中国的建筑交流史

“穿越边界:日本建筑展”展示风景
所有照片:作者提供
穿越边界的建筑师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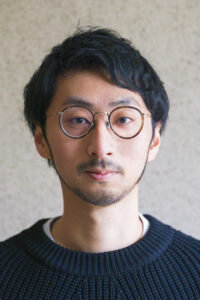
市川纮司(建筑史学家)
为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深圳的文化综合设施“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了日本建筑师的作品展“穿越边界:日本建筑展”(时间:2022年11月5日~2023年2月19日)。首先介绍一下该展会。
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深圳设计互联联合举办的本次展览,如标题所示,聚焦了日本建筑师们的“穿越边界的作品”。展会大致由两部分构成。首先,以1960年代开始活跃的槙文彦和矶崎新为首,还有安藤忠雄、伊东丰雄、坂茂、隈研吾、石上纯也、藤本壮介等活跃在世界各地的8名建筑家的模型和装置艺术。另外,田根刚和大西麻贵+百田有希(o+h),以及以电视演出为契机在中国享有超级知名度的青山周平等年轻到中坚层建筑师的面板展示。会场设计由中国年轻建筑师fan亲手打造。悬挂半透明的隔板,用自由曲线松散地划分展示区。空间的气氛,很好地表现着纤细、柔软、白色、边界的暧昧性等现代日本建筑的最大公约数的特征(用树组成的什器设计由在中国活跃的东福大辅设计)。
策展人是华盛顿大学的建筑学者大岛正。大岛正也曾在金泽建筑馆策划了该宗旨的展览会,本展被定位为其升级版。大幅度的变更点是,核心展示的8名建筑家分别展出了至少一个在中国的项目。例如,槙文彦展示了会场“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安藤忠雄展示了广东省同心圆重叠状的美术馆(“和美术馆”),石上纯也展示了山东省森林中的幼儿园(“森林幼儿园”)。伊东丰雄在国际上很活跃,但其实此前在中国并没有实际作品,本展展出了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浙江省图书馆项目(“宁波华茂教育图书馆”)。另外,伊东在19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的家具作品《东京游牧少女的之包》复原再制作也值得关注。在香港建成的新美术馆M+中,移建收藏了仓俣史朗的泡沫经济时期寿司店的整个室内装饰,对当时消费社会全盛的日本设计的关注十分高涨。
相反,从展示作品来看,代表日本的建筑家们都在中国有自己的作品 。也看出中国如此积极地接纳了日本建筑师们。原本日本的建筑家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的普利茨克奖的获奖者也很多,在国际上评价很高,但是像中国这样聚集了“超越边界的日本建筑”的地方并不多吧(当然中国的市场本身的体积也很大)。
如上所述,本展由国际交流基金联合举办,被定位为日本政府实施的各种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事业之一(事业阵容可以在外务省网站上确认)。在这样的“周年纪念事业”中,建筑被大肆推出似乎是第一次。无疑,日本建筑师在中国的显著活跃是最大的理由,或者艺术表现中建筑的某种“异质”也是这次聚焦的一个原因。美术和电影等也是日中交流盛行的类别,但由于政治主张经常被焦点化,所以在言论管控日益增强的现习近平时代,这些类别不适合官方纪念事业。在这一点上,建筑被称为艺术中最“不纯”的类别,由于受到人、金钱、时间、制度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干涉而产生的,因此也很难说是能表现纯粹政治性的类别。如果建筑在根源上有这样的“不纯”,而结果作为纪念事业促成了本展会的话也是饶有兴趣之处。
从中国看日本:从技术领先到设计合作伙伴

“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1990)
追溯日本建筑师在中国的活动,可以发现开端是经过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实施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项目的性质和规模虽然各有不同,不过,大致以1990年代末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80~90年代引人注目的是有规模的设计事务所和综合建筑商的项目。以大成建设公司的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1986)、日本设计建设的宾馆和办公室的综合设施“北京京广中心”(1990)、森大厦·藤田·大林组建设的“上海森茂国际大厦”(1998)等大规模具有综合功能的超高层建筑为主。京广中心高达208米,是2005年以前北京最高的建筑物。
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超高层建筑的圣地,但经过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高层建筑的技术积累。回避作为资本主义标志的高层建筑是很大的理由。因此,中国向日本和欧美的建筑企业寻求的,首先是发挥现代先进的西方建筑技术的先导作用。
外国企业在进行建筑项目时,一般都会与具有当地建筑相关资格、符合当地规则和习惯的当地企业合作。在中国关于资格的限制特别强。因此,在上述项目中,例如京广中心的正确设计者信用也需要加入中方的组织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在这样具体的合作关系中,中国的设计者和施工学习了日本的技术和诀窍。
至少在建筑领域,当时的两国关系被简单地描绘为“日本在教/中国在学”。为亚运会而建的北京“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1990,照片),或许可以说是体现该关系的建筑。被选为“北京十大建筑(1990年代)”的国家建筑,其特征是将屋顶像吊桥般吊起来的设计,一看就知道,原型是丹下健三的代代木体育馆。实际上,设计者是在丹下事务所实习过设计者的设计。尽管如此,与代代木的优雅设计相去甚远的略显笨重的建筑设计。在20世纪末的日中之间,设计技能和施工技术有很大的差距。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终于像“超越边界:日本建筑展”上介绍的那样,工作室派建筑家在中国的项目在增加。他们被期待所发挥得作用与其说是技术上的先导,不如说是提高建筑设计价值的设计师。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中央电视台(CCTV)新办公楼等国家项目上可以看出,外国建筑师大展身手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隈研吾“竹之家”(2002)
在中国活跃的日本建筑师很多,其中矶崎新和隈研吾的存在很出色。
矶崎新的“深圳文化中心”(2008),是在中国最初通过正式的国际设计竞标建设的图书馆·剧场设施,象波浪流动的玻璃的外立面和金色闪耀树木般的构造十分独特。矶崎在其他中国的主要大城市设计了很多大规模的文化设施,可以说2000年代以后他的工作集中在中国。值得一提得是四川省“日本侵华罪行馆”(2015),是当年日本建筑师设计抗日战争相关展览设施极为罕见的案例。正如《再次成为废墟的广岛》(1968)的作品那样,在投下原子弹后的广岛废墟上拼贴出未来城市图片。1931年出生的矶崎亲手制作了很多与二战相关的作品。
隈研吾是代表当代日本的建筑师,在中国的项目量也是出类拔萃的。在中国的出道之作是2002年竣工的“竹之家”(照片)。这是民企开发商SOHO中国(当时红石公司)在万里长城附近开发的别墅地“长城脚下的公社”之一栋,日本女演员吉永小百合在此拍摄的电视广告在日本也很有名。大胆使用中国竹子的素朴的空间表现受到了高度评价。此后,同一客户的“三里屯SOHO”(2010)、“虹口SOHO”(2015)、代表中国IT企业的阿里巴巴总部大楼“阿里巴巴集团淘宝城”(2013)等作品不断诞生。
从日本看中国:建筑媒体的关注

赵扬“气仙沼市共有之家”(2013)
相反,中国建筑师们的作品在日本能看到多少呢?
比较著名的有,东日本大地震的复兴建筑(集会场)而建造的云南年轻建筑师赵扬的“气仙沼市共有之家”(2013,照片),还有日本的早野洋介也是成员的MAD建筑事务所以人字形屋顶要融化般的曲面屋顶为特征的住宅兼幼儿园“四叶草之家”(2015)。在“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MAD还设计了激活清津峡隧道风景的装置艺术。这在现在看来是该艺术节的招牌作品之一。来自苏州、以美国为活动地的贝聿铭的“MIHO博物馆”(1997),也可以作为中华系建筑家的日本项目的先驱例子。但是,中国建筑师的作品在日本还几乎没有建出来。原因是日本由于国内的建筑师和建筑企业已经成熟,所以外国建筑师的工作相当有限。一般要求的都是国际明星建筑师的品牌力量,而委托在国际舞台上活跃较少的中国建筑师的优先度自然很低。
但是,并非建筑界对中国的关心低。把目光放到亚洲,回顾其历史,对中国建筑关注度在20世纪80年代很高涨。日本建筑学会于1986年迎来了创立100周年,作为纪念事业,从亚洲邀请了很多建筑相关人员的“亚洲建筑交流国际论坛”,那是象征着“亚洲热”的时代。此后,民间的建筑专门杂志也不断推出香港、台湾、印度尼西亚等专题报道。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从经济成长的东亚到东南亚,这个时期在日本很热衷对经济、文化的交流。
而在2000年代,日本建筑师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对现代中国的关注也迎来了高峰。综上所述,当时建筑媒体对中国的焦点集中在两点。第一,在快速增长的中国,城市将如何变化。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建筑师正在实施什么样的项目。
这种对“沸腾中国”的好奇心和对日本从中获得的实际利益的期待,不仅仅停留在建筑界。实际上,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正在经经历建筑泡沫期。2007年,位于东京乃木坂的建筑专业画廊TOTO画廊“间”,选中在北京刚开始活动的两名年轻建筑师(迫庆一郎和松原弘典)开展会。展示了和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年轻人手的数量庞大、规模空前的项目在中国却随处可见,这样的状况很是刺激。
进入2010年代,建筑师的固有名字终于为人所知。著名的有作为中国建筑师在2012年首次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王澍。最近,回顾他的建筑观和设计手法的著作被翻译出版的(《造房子》),这是第一本能用日语阅读的中国建筑师的思想书。上述MAD建筑事务所出版制作日英双语杂志《a+u》推出专题报道。另外,艾未未是一位拥有激进分子面孔的现代美术家,实际上作为建筑师也在精力充沛地活动(虽然近年来作品很少)。和美术作品一样,属于注重细节的极简主义风格,在创意阶段也参与了北京奥运会“鸟巢”的设计。这样的建筑作品在森美术馆的大规模个展(2009)中也有介绍。
走向边缘交流
概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接受日本建筑,以及日本接受中国建筑的历史。最后,让我们阐述一些今后的展望和课题。
日中两国哪一方在积极接纳对方显而易见,不过,今后该倾向也会继续。以上没有提及,在中国不仅有众多日本建筑师的项目,对历史书和作品集的翻译以及举办建筑师展也非常积极。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等地,石上纯也、伊东丰雄、筱原一男等建筑师的个展每年都会举办,各展的内容充实程度甚至超过了日本。包括中国展览在内的建筑媒体活动,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差距将越来越大。
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事业的“穿越边界:日本建筑展”,被定位为如此浓厚的中国现代日本建筑接纳史的一页。今后的课题是,借此机会设置两国建筑师水平交流的平台。不仅仅是向中国介绍日本的明星建筑师,也要在某些主题下进行对话。因为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建筑师们的工作从2010年代后期开始急速拓宽。不仅设计了巨大的开发项目,极小规模的店铺室内装饰和改建,农村的社区设计工作也不在少数(背景有习近平政权的新型城市化政策)。相反,东日本大地震以后的日本,这种倾向也很明显。也就是说,两国的建筑师具有同时代性。与“不景气的日本”和“泡沫经济的中国”这两个和2000年代以前的关系不同,两国建筑师的对话终于到了不需要依赖“日中交流”这一题目,进入了可以有具体课题和方法论的阶段。
从事这种拓宽性工作的建筑师,在日本和中国都不是明星建筑师,有年轻人和在地方居住者等,从建设业界整体来看是周边的存在。同是周边的人会或许互相会感到很亲近。在关注超越边界活跃的全球精英的建筑师的同时,也期待同是边缘的建筑师彼此接触,撼动边界和边缘。
本文所概述的两国间建筑交流也需要进一步的历史性的验证。
本稿只提及了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交流史,但并非此前完全没有。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建筑学家西山夘三在20世纪60年代初访问了中国不到一个月,与中国建筑学会的各位人士进行了交流。在日本建筑界看来,这是一个可以直接进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和城市规划思想的机会,而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可以取代关系恶化的苏联结交发达国家合作伙伴的机会。结果这宝贵的交流机会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成果,但如果顺利地继续交流的话,会对以后的两国现代建筑产生不小的影响吧。
上文提到,日本建筑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正式关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事实上,旧殖民地建筑研究等也从那个时期开始终于有了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建筑媒体中,由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亚洲几乎没有成为话题。但是,是不是完全没有项目的呢?也不完全是。综合建筑开发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以战后赔偿事业为契机陆续进入东南亚。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国,作为赔偿的替代实施了的庞大的ODA(政府开发援助)事业,实施了比如黑川纪章设计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1990,照片)等多项建筑·基础设施建设。有趣的是,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项目的相关人员和开发手法具有战前殖民地建设的连续性。

黑川纪章设计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1990)
正如开头所述,建筑是与社会和经济深深融合的“不纯”艺术,因此不适合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但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理由,也蕴含着在外交战略中茁壮成长,意想不到的历史连续性。日中之间的建筑交流史,不仅仅有建筑师的华丽作品,那些政策性的项目也应该放在其中被记录下来。
[月刊杂志《世界》2023年2月号《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与中国的建筑交流史》得到笔者以及出版社岩波书店的许可翻译、转载。]